如何透过“虚开*”表象揭示费用支出性质实质
----由一宗唐山某国企因“虚开发票”引发补缴企业所得税诉讼案想到的
2018年9月,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国家税务总局唐山市税务局 稽查局与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税务处理决定二审行政判决书》(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8)冀02行终474号),该案经一审二审最终尘埃落定。网上对此案的判决基本是形同水火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有的支持判决,认为是落实了税法精神;有的认为是冲击了税务管理制度助长了发票虚开并使税收文件陷入尴尬境地。笔者作为税法爱好者,倒是愿意站在另一个角度跳出“虚开发票和税收文件”这个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对案件的实际深入了解,其实我们的讨论是很肤浅的可能也是片面的,甚至可能会被判决书反映出的与实际问题存在一定程度偏差的内容所误导而导致结论荒谬。即便如此,我们虽然不得而知该案件争议背后的具体情况,还是有必要做一个很浅显的研究,毕竟这可能会有益于推动税法的规范和进步。透过近万字的判决书内容来看,笔者认为该案最应考虑的最基本也是最尖锐问题其实似乎不应仅是对“虚开发票”的定性问题,以及对企业虚开之下实际发生费用的税前扣除问题。掩卷深思,我们似乎更应站在更高的逆向思维视角来重新客观冷静地审视这个税务争议,而不应直接陷入这个案件的是是非非中迷失方向,局限于对某些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无休止讨论。事实上,法院基本也是按照这个方法来剖析问题实质并阐述这宗税案的说理理由的。
一、案件讨论的前提条件是可以按照“税法”精神研究案情。
我们不妨大胆假设,假定纳税人不以“虚开发票”套现资金而是通过其他虽也不为税法所允许但却可有效避免直接强烈刺激税务部门敏感神经方式获取资金并发给工人,该实际发生的费用能否税前扣除?这应当是个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相比之直接讨论虚开发票如何税务处理和什么样的工资支出才属于可以税前扣除更能切中要害直奔主题,更能从根源上判定涉税交易的定性问题,更能一竿子到底在争锋相对的观点碰撞中找到法律根源,也更具有拨云见日化繁为简的现实意义。
在讨论之前,首先必须清楚,如果说税法明确规定了纳税人只有通过法定渠道获得资金支付的费用,才能在税前得到扣除。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根本没有任何讨论余地,也无法展开讨论。
其次更要知道税务对费用支出判定的底线,如果说纳税人发生的实际支出只有符合税务机关按照自己对税法的理解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所规制的“形式要件”外观要求,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予以扣除,并且惟其如此才算合法,那么这个问题其实也根本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
再次还必须搞准对纳税人真实发生的业务税务部门在判定是否可以税前扣除时还有没有自己在税法之外的规定。如果说纳税人发生的实际支出只有符合税务机关按照自己对税法理解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所规制的“形式要件”外观要求,并还需进一步考虑该费用是否真实发生、是否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且合理,是否属于必要的合理支出,那么这个问题仍不具讨论的可能性。果真如此,不要说被判定为“虚开发票”这样为税法所坚决禁止的违法行为,即便就是交易手段合法却未能按照税务机关规定交易路径、方式并且还要在外观形式上符合税务明文规定的支出,也是不能扣除的。一句话,只要不是按照税务机关对某项具体费用支出的判定标准来支付费用,哪怕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也会在税务机关一丝不苟地对照文件照本宣科式筛选之下不被税前扣除,那么即便考虑了费用支出的“合理性、关联性”,本案仍还不具备讨论的可能性,因为在一边倒的政策规则之下,是没有讨论是非曲直的可能的。
最后,如果有这样一个可能,即能抛开上述税务部门的强制性专门文件规定,能在不设限定条件前提之下按照税法层面平等讨论,如果企业发生的实际支出虽不符合税务机关规范性文件具体规定,但是却能够符合税法关于可以税前列支费用的基本原则,而仅是需要考虑该费用发生与取得收入的“关联性、合理性”,那么这个案例才具有讨论的可能性,也才具备可以讨论的价值,也才能继续为下一步在技术上深入讨论铺平道路。当然这就必然直接指向下一个敏感问题,即税法的实际执行到底是以“法律”为准,还是以部门文件具体规定为准。
二、当税务部门执行仍属有效却可能对纳税人权利做出了限缩性规定的文件被纳税人质疑时,是按照该可能存有瑕疵的文件执行,还是按照税法执行。
这是个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的税法体系包括税法、法律、规章、规范性文件。当文件未被宣告失效时仍应属广义上合法的税收法律,仍应得到尊重并被继续执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受政策制定者眼界、学识、经验、思维和当时客观存在的各种能对政策制定施加影响的来自社会的、政治的、人为的等因素干扰,某些政策与生俱来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税法原意和立法主旨,没人敢保证税收规范性文件能永远完全精准地契合税法精神,没有违背立法原意而做出了限缩性或扩大性的解释或规定,当其被具体执行被提出质疑并明显与上位法相冲突时如何避让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如果纳税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持上位法占据法律制高点据理力争,而守土有责的税务机关持可能存在瑕疵但仍属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寸步不让,矛盾就会尖锐对立,并最终可能就只能依赖法律来平衡。那么,这就必然会涉及到一个“法律避让”问题。在官民平等的法律评价体系面前,“狭路相逢”未必永远是“勇者胜”,也未必一定是“强者胜”,而最终应当只能是“智者胜”“守法者胜”。这应当是法治社会背景下的历史大趋势是大概率事件。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也不能保证每个案件判决结果都能很好彰显这一精神,但法治毕竟会成为一种潮流。十八大后,“税收法定”更为依法治税提供了方向。一般而言,法律避让应遵循“下位法让位于上位法”,但同时也必须遵循“一般法让位于特别法”原则。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特别法”很多,但关键是“特别法”的名义并不能滥用。什么样的法律才是法律上承认的“特别法”,税收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法律体系中的“特别法”,法院判决是否承认这一定位,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讨论案情之前就必须搞清楚。
第一个问题,“特别法”应当是仅适用于特别的法律关系主体、特别时间、特别地区的法律。它首先必须是个法律,而不是规范性文件。适用于全国的法律称一般法,仅适用于某一地区的法律称特别法;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法律称一般法,仅对部分人有效的法律称特别法;对一般事项有效的法律称一般法,仅对特定事项有效的法律称特别法。对于企业所得税而言,目前就仅有一个法律即《企业所得税法》,而并无其他特别法存在;在其之下有《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这个法规;在法规之下有《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在规章之下还有各种繁杂浩瀚的关于资产、成本、费用税前扣除的专门文件。如果说有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特别规定,也仅有《房地产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财税(2009)31号文),但它并不是法律,如果与上位法《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条例》相抵触,也必须无条件执行上位法。因此可知,相对企业所得税法而言根本就没有特别法,它就是为一个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唯一“税法”。处于法律体系中最低位置仅是作为执行政策的操作性规定的文件更要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的精神、外延而存在,否则即是无效的。由此,在《企业所得税法》面前,任何与本税种相关的税收法规、规章、文件都要依法无条件主动“避让”。
第二个问题,法院审理案件依据的就是法律、法规,参照规章。作为审判定案依据,税收规范性文件根本就难以直接进入法官的法眼,即便它是完美无缺的。法院可以直接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判决案件,而可以不去理会规范性文件,至多参照规章即可。这是再正常不过也无可厚非的法律判决游戏规则。即便遇到复杂事项,需要碰触到“规范性文件”这一层级,法院也是有权而且必须进行审查的,而不一定就立刻乖乖地被“规范性文件”牵着鼻子走,直接按照“规范性文件规定”判案。只有符合法律精神的规范性文件才会被法院引用。这一点在法律的使用上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以下简称1号文)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合法的,应当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经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人民法院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在裁判理由中予以阐明。做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应当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并可以抄送制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上一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备案机关”。而且,一般而言,法院不会主动陷入对规范性文件的纠缠中。只有特定情形发生,才会碰触“规范性文件”,而且只对符合审查申请条件的规范性文件按规定程序审查。1号文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一并请求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审查的,由行政行为案件管辖法院一并审查”。1号文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审查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基于上述规定,只有在一审时已经提出了“审查规范性文件请求”的,法院才会对其合法性审查,而且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审查,而不是随心所欲地判断,这在1号文第一百四十七条有明确规定,其规定:“ 人民法院在对规范性文件审查过程中,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不合法的,应当听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意见。制定机关申请出庭陈述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行政机关未陈述意见或者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不能阻止人民法院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就本案而言,如果唐山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税务机关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就必须启动审查程序并听取国家税务总局的意见。如果案件当事人未要求法院审查规范性文件合法性,法院可以不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可不引用,而大可径直引用法律、法规并参照规章判案。同时,它也因为未对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能将其“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哪怕这个文件事实上是真正合法的,它也只能被弃置一边而直接被更高层级的法律法规或规章所“淹没”。只要无审查文件申请,法院就完全可以利用稳定性最强的法律法规或参照规章直接作为定性依据。而且,在裁判文书中引用规范性文件也不宜作宽泛的理解。引用规范性文件的前提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没有规定,根据法律精神和原则也不能做出相应判断。如果法律、法规、规章有相应规定或根据法律精神和原则可以做出明确判断,则不能直接引用规范性文件。就本案而言,《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第十条对税前扣除已经具有明确的规定,《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又做了具体规定,根本不存在扣除原则和精神不明确之处,根本无需通过规范性的规定来填补。法院判决对哪怕经过审查确实合法的规范性文件也只能在说理部分阐述引用,最终判决还要依靠法律法规或参照规章判决,毕竟这才是一个十拿九稳无懈可击的方案,也是最为便捷、最为安全的趋利避害的方案。
上述道理,税务机关未必不懂。虽然如此,但是,必须承认因担心对税法原则和精神把握不准,每个敬业的谨小慎微的执法者都愿意依赖规范性文件来解决实际遇到的疑难问题,毕竟这样可以做到“法有明文”,可以对号入座,执行政策到位,这完全是强烈的责任心和风险意识使然。退一步讲,即便政策文件被法院判决违法,执法者也会毫发无损,他毕竟没有自作主张渎职失职。当然,这个安全需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涉税事项必须符合税收文件适用的条件,如果生搬硬套或者张冠李戴仍是违法的。既然,我们都认可将问题交给税法来裁决,而且规范性文件又必须服从税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问题的终点,进一步对税法关于税前扣除原则进行研究。
三、企业所得税法、法规、规章对税前扣除费用的原则是具体的,任何单位不能对其做出限缩性或扩大化解释和规定。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 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个规定突出了可以扣除的费用必须具有“实际发生”这一特性,不能虚构,而且必须具有“相关性”,更进一步讲,并非与取得收入有关就行,还必须在理由上做到“合理”。为了便于对该条款的理解,其又对费用扣除以正列举方式明确做出了“禁止性”规定。第十条规定:“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一)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二)企业所得税税款;(三)税收滞纳金;(四)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五)本法第九条规定以外的捐赠支出; (六)赞助支出;(七)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 (八)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应当说这两个条款是珠联璧合的,特别是第十条第八项规定,又完全暗合了第八条规定,即“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肯定不能税前扣除。这样,通过第八、第十条两个条款一正一反就完全在法律层面锁定了费用扣除的“相关性”这一最基本扣除原则。为强化这一原则,《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又进一步细化了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有关的支出,是指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所称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至此,费用扣除原则在法律层面规定得已经非常准确,即“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且“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按照哲学观点来讲,事务是普遍联系的。与取得收入相关的费用很多,但是税法始终坚持在费用扣除原则上只有“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才具有扣除的可能性;而且,对“直接相关的费用”也必须去伪存真,只有经过调查分析判断“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的才真正能够得到扣除。作为规章,《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税务总局2018年第28号公告)第四条规定:“ 税前扣除凭证在管理中遵循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真实性是指税前扣除凭证反映的经济业务真实,且支出已经实际发生;合法性是指税前扣除凭证的形式、来源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关联性是指税前扣除凭证与其反映的支出相关联且有证明力”。这一规定,对费用扣除凭证的来源、外观、证明效力均做出了强制性规定,即凭证内容必须“保真”,凭证取得必须“合法”,凭证能佐证入账扣除费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为纳税人不能偏离这一原则虚构证据或非法取得证据或使用无效证据将费用入账扣除;作为税务机关也不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据规范之外再自创税务部门规定的证据。只要企业证据符合《证据法》、《发票办法》、企业会计法律法规制度等法律法规即应予以认可。
就本案而言,企业是以“实际发生的工资支出”名义进行扣除的,那么这就必然会涉及到有关税法、法规、规章的具体规定了。我们未见到纳税人关于扣除工资的证据,但是只要它能够首先证明这个工资真实发生了,发给在这个纳税阶段工作的本企业职工了,其次能够证明发放的工资是与取得收入有关的,是给直接从事生产经营的职工的,不是给三产的、离退休等其他无关人员,再次能证明所发的工资不是滥发的,是有据可靠有案可查的,最后这个工资入账凭证的编制也完全符合会计制度规定规范即可。那么,这个工资的扣除就是合法的。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规章,对于扣除费用均是考究其发生的真实性、合理性、关联性,而并没有对发生费用的资金来源渠道做出限制性禁止性规定,并未要求支付费用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不能是借款;支付手段必须直接支付不能委托支付。所有这些细节其实才应是本案真正技术层面争议的核心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可以按照上述税法、法规、规章规定的精神来解决这个纷争,那么我们才有可能继续深入研究下一个有点“扑朔迷离”的问题,也就是导致税企双方各执一词并在理解上大相径庭渐行渐远的表象问题,也才能揭开这团障眼的“迷雾”。
四、扣除费用的税务审查是看外观形式,还是看实际内容;是考究费用发生的真实性,还是追究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毋庸讳言,综上所述,费用扣除的审查重在看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合理”、是否“与取得收入直接关联”。如果偏离这个主线剑走偏锋,就必然会离题万里。所幸的是,法院牢牢把握住了这个主线,直接切入了主题,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企业职工工资的合理性与工资资金的来源方式是否合法没有必然联系”,并且明确判定“企业职工取得必要的、适当的工资收入既合法又合理。”有了这个法律判定,税前扣除工资费用就没有任何法律障碍了。
不得不提的是,法院也应当是经过认真分析研判,才能“拨云见日”,透过“虚开发票”这一表象来得到“原告虚开发票套取本企业资金,其行为违法并不必然导致原告使用套取的资金给职工发放工资违法”这一正确论断的。法院分析论证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判决结论一锤定音消争止息。但是,在这个结论形成之前,毕竟还有“虚开发票”和“支付工资”两个问题同时存在需要进行税务定性的问题。那么,这又必然会涉及到一个分析研究问题方法论的问题,一个如何把握事务整体与局部的问题。
如果站在局部角度看待问题,其一,纳税人虚开发票毫无争议,其二、他又同时支付了本企业职工的工资也无法否认。如果将其看成是两个孤立的互不相关的个体事件,必然就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虚开发票目的必然是为了“虚增”费用税前扣除,具有《税收征管法》第63条所列情形而成为涉嫌“偷税”案件;而发放工资又必然因为“虚开发票”已经是一个虚构事件,这个费用不存在发生的“真实可能性”,更不要说“合理性”和“关联性”了。这两个事件同时并存,纳税人很难做出两者都是合理存在的解释。退一步讲,如果允许纳税人只对其中一个事件进行合理解释,那么“虚开发票”根本见不得阳光一捅即破,而“发放工资”又因为已经有了先其存在的“虚假的劳务费用”发生而根本就没有再重复列支的可能性。如此一来,即便你实际发给了工人工资,也难以做出合理解释。这就是税务机关穷追猛打的思维根源。至于再坚持工资支出的扣除必须符合税务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那其实已经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了,是一个在法院判决时并非占据举足轻重位置的技术问题了。
如果站在全局角度考虑问题,将“虚开发票”与“发放本企业职工工资”两个事件结合起来研究,那么就会另有一番天地。
首先,必须考究“虚开发票”的背景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手段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如果纳税人就是无中生有想虚列费用降低利润且已经将其进入成本在税前扣除,那么“偷税”即可形成,该“虚开发票”行为不但违背了《税收征管法》第63条要对虚开部分合并利润征企业所得税,而且还要处罚;同时,还要按照《发票管理办法》对该行为本身进行处罚。如果不是这个目的,也并未形成这个结果,就需要重新审视这一行为。如事实真如判决书中所透漏信息所言,纳税人并非是为了通过“虚开发票”套现留在企业不动或者私分或者贪污,而仅是利用“虚开发票套得资金”用于了生产经营,那么问题的性质就有了改变。
其次,必须考究“虚开发票”与“发放工资”是并列关系,还是“吸收”关系。如果是并列关系,则当然虚列费用属于偷税行为。如果是“吸收”关系,即发放工资的真实结果吸收了“虚开发票”的表象,则它又变成为一个“资金来源问题”,而不是“税前扣除合法性问题”了。正如案件中的说理解释一样,如果“虚开发票”仅是为了规避纳税人客观存在的资金监管而不得不为之的手段之一,那么这个“虚开发票”不过是一个幌子,一个为达到获取发放工资目的而采取“曲线救国”方式的一个不合法手段而已,这与企业违反财务制度规定直接在生产费用中提取“工资性绩效基金”而后发放是异曲同工之效,与“虚列生产费用套现再实际发给职工”更是殊途同归。当然,不可否认这些手段同样都是违法的,只是比“虚开发票”更隐蔽些。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纳税人这样煞费违法苦心套现来发放工资应当是有“难言之隐”的,是不得不采取“走钢丝”的下策的。纳税人最终目的是为了“发放工资”,而不是“虚列这个费用”而将资金实际留在企业不动。实际发放工资是目的和结果,“虚开发票”不过是获取资金的手段和过程,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在企业财务监管体制下可以合理套取资金的“合法外衣”。这才应当是一个事件的整体。如果深刻而透彻地在宏观上把握住这一点,那么就必然得出纳税人是“利用违法手段获取资金却合法支付了工资”的完整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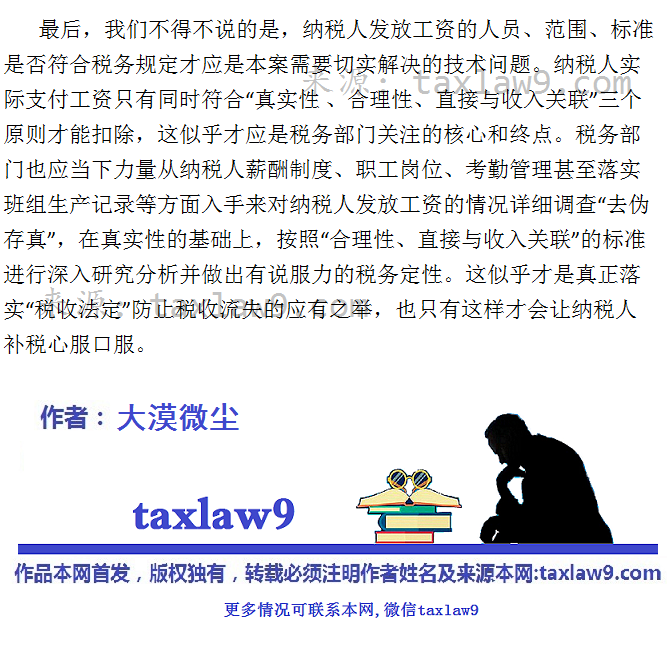
推荐
-

-

QQ空间
-

新浪微博
-

人人网
-

豆瓣




